文章信息
- 赖敏, 贾春华, 徐爽.
- LAI Min, JIA Chunhua, XU Shuang.
- 基于概念隐喻分析“心主神”理论的形成
-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heart dominating mind"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
- 天津中医药, 2024, 41(1): 39-43
- Tianji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4, 41(1): 39-43
- http://dx.doi.org/10.11656/j.issn.1672-1519.2024.01.09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23-09-26
围绕心与脑孰主神这一问题,中医学者对“心为何主神”进行了诸多讨论。其中大多学者将心主血作为心主神的前提[1-2],认为精神紧张、神志不安等伴有心跳、脉率加快是促使人们认识到心神关系的重要因素[3-4]。但实际上血脉遍行全身,古代医家并未将心看作经脉循环系统的中心;廖育群指出中国古代医学中“胃”是气血生成与运行等生理活动的中心,而“左乳下”的心尖搏动被解释为“胃之大络”的跳动[5]。从神与血、脉的密切关系出发似乎更应形成“胃主神”理论。有学者认为心因居于人体正中而备受重视,成为人体的主宰,与神为自然、人之主宰相结合成为主神之官[6],并提出“心主神”实质上是“五脏中心主神”,不仅有心主神,亦有脾主神之义[7]。古代典籍确有心居中与脾居中而分别与土行相配的记载,却并未提出“脾主神”,位置居中虽可说明心脾的重要地位,但不足以解释心主神的独特性。
早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即有心神关系的诸多论述,且常常与感官同时提及。中国早期思想史研究指出感官活动不仅为认知活动提供质料,也提供了原初的范型,从而塑造现实的认知方式[8]。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概念隐喻在中医藏象学说中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本文从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出发,结合古代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以及生活实践经验,阐释感官与心、神之间的深刻关系,及其如何影响“心主神”理论形成,以期更好地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与价值。
1 感官七窍与神莱考夫指出若不借助隐喻方式把心智的各方面加以概念化,那么思考和谈论心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9]。人们对神的思考和认识也需借助多重的隐喻系统加以概念化,感官为精神活动提供质料,是表达构建认知、思维、道德、审美等心智活动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概念和载体。
1.1 感官七窍与认知思维人们依赖于感官来获取信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口(舌)之所尝等则是人们所知、所识。如中医五味理论是以原始滋味说为基础逐渐发展形成的,先秦之前药食的滋味就已成为认识和描述其作用或毒性的首要标志[10]。关于目、视觉与认识的关系,严健民从考古和先秦史料中目、眸、瞳及由目演绎的“(臣)”字内涵探讨人的思维功能,认为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过程中潜藏“目主思维”过程[11]。《论语·述而》篇云“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认为闻与见都是认识学习的重要途径;《论语·里仁》篇亦云“朝闻道,夕死可矣”,“闻”不仅指听到,也包含所闻之道被理解、认识,使人有所得而影响其信念和行为。《墨子·经说下》云“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唯以五路智。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不仅认为目之所见构成人的智识,还指出通过5种感官经验获得知识的方式为五路智,五路即五官,包括眼、耳、鼻、舌、身。其中都蕴含了“认识、理解、思考是尝到、看到、听到”的隐喻。感官不仅是获取信息的通道,围绕感官形成的各种概念也是人们组织知识体系、表达认识思维的基础。不仅如此,感官活动甚至塑造了人们的经验和认知方式,以视觉为主导的认知活动强调物我疏离、对事物界限的辨析以及确定性形式的把握,而以味觉为主导的认知活动则以拉近弥缝物我距离、主客相互交融为特征[12]。
1.2 感官七窍与道德审美道德审美代表了古人的心灵生活和精神世界,而感官七窍也部分地构建了人们对审美、道德的认识和理解。《说文·羊部》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的感受最初来自食物的甘甜滋味。华夏审美文化可能首先注重的是“味觉美”,逐渐向视听之美拓展,形成了以听觉、味觉、视觉、触觉、动觉、言语等交融的“综合的审美感受”[13]。另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对七窍所感之味色声的规范则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离娄上》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公孙丑上》亦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指出从眼睛的明亮昏暗和言辞内容可以了解人的道德品性和内心世界。
感官七窍与认识、思维、道德、审美等概念的构建关系密切,被认为是精神、神明的门窗,是神往来活动的通道,如《淮南子·精神训》云“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韩非子·喻老》亦云“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说明古人通过感官七窍来观察、认识和表达神的内涵。
2 “司外揣内”的认知模式第二代认知科学强调心智具有亲身性,概念与理性以我们身体、大脑的特性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为基础[9]。在人类早期的日常生活与医疗实践中,人们对人体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多是由外到内的,如殷商时期对人体体表的头面、四肢、躯干等不同部位均赋予了许多专名,而对人体内部的脏腑组织记录甚少[14];在《五十二病方》中有病名103个,其中外科疾病和皮肤科疾病就有90个[15]。《灵枢·外揣》所云“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以日月、水镜、鼓响与影、形、声内外相应为例阐释如何把握复杂事物。杨上善谓“远者所司在外,以感于内,近者所司在内,以应于外”,因内外相应,以所司一面揣度另一面,蕴含着根据所处情形,以熟悉了解的对象认识把握与其相应而不可知的对象。“司外揣内”不仅是一种由人体外在症状表现推测机体内部情况的诊断思维方法,也是古代人们认识人体内部的一种认知思维方式。在内外相应、天人合一思想下进行取象比类,取象比类即“中国式隐喻”[16],隐喻将熟悉的自身感觉经验作为始源域,寻求理解说明的陌生事物作为目标域[17]。由人体外部到人体内部,即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途径和思维模式决定了在人类早期认识活动中,外部肢体、感官七窍的活动结构是人们理解内部脏腑和精神世界的基础。
3 心之七窍与神心是人们较早通过解剖认识到的脏器之一。早在殷商末期人们就完成了心脏的大体解剖并造字,“心”字甲骨文先后写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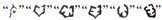
心的孔窍与神的关系同样密切,如“圣人心有七窍”,其中蕴含心窍的数目是圣人本质特点的体现。“圣”的甲骨文作“

古代文献中常能看到感官七窍与心、神相关的诸多论述,如《灵枢·大惑论》言“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神舍于心内而心能驱使目感知外物;《文子·道德》云“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庄子·人间世》亦云“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觉作为一种感官,脱离了耳的束缚,成为心、神、气的功能,表达更深层的思考和领悟。说明感官不仅是认识和表达心、神功能的重要概念,也起到了串联心、神的作用。中国古代哲学中神的含义由天神到天地万物的主宰或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都未脱出主宰之义[7]。神由天地万物的主宰到人体的主宰,表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心的主宰地位来自于神的迁移,心的主宰对象由五官扩展至脏腑以及全身。如《荀子·天论》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心治五官而为天君;《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云“一国之君……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以身喻国,君若心以治内外,内外即包括脏腑和形体孔窍。
感官是人们认识神的通道,但神的显现又不止于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缤纷多样的自然万物和感触经验通过感官进入人的思维意识,精神无形可见而神秘莫测,但又时时控制着人们的感官与行为,即使闭塞了感官,精神活动仍然存在;精神的异常则表现为人的行为、语言等失去控制。因此远古中医学思想萌芽过程中虽然潜藏着“目主思维”的过程[15],但古人对思维脏器的认识不停留于人的感官。在观察人体内在脏腑组织过程中,心的多孔窍结构受到人们的关注,心之七窍与感官七窍的形似,启发促进了“心主神”理论形成。感官七窍,是神往来的通道,心为神之居处,心之七窍则是神出入活动的地方。
5 从“心-神-窍”关系论心藏象理论之争议 5.1 从“心-神-窍”关系论心开窍之官相较于其余四脏,心与感官七窍均有直接联系。如《素问·解精微论》云“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云“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心主血,血生脾,心主舌……在窍为舌,在味为苦”;《难经·四十难》言“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除《难经》指出鼻之嗅觉与心有关,《黄帝内经》则明言为心之窍者即有“目”“耳”“舌”。神居于心,任物-意-志-思-虑-智的整个认知过程由心神主导[17],形成认知的信息由五官传递给心神。因此,在脏腑与官窍的配属中,心藏神是心之窍分别为“舌”、为“耳”、为“目”的重要背景和出发点[21],这也是“心-神-窍”关系在中医理论中的部分体现。
心与耳、目、舌分别配属,而为何最终形成“心开窍于舌”的主流观点。这或许从不同感官对中国古代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解释,能够得到更好的回答。中国思想史上存在不同感官交替优先的认知取向,从商周至秦汉时期,经历了以耳口通达内外的认知传统,到先秦时期耳目被突出,最终至秦汉时期确立了味觉优先的认知取向[8]。因此心开窍于舌,不仅是目耳口鼻为四,与五脏数量上无法一一对应的折中处理,更是在感官的认知取向发展过程中,人们重视味觉活动,以致舌的认知地位逐渐突显的结果。
5.2 从“心-神-窍”关系论“心主神”与“脑主神”之选择古代人们通过感官七窍来理解和表达人的精神世界,现代脑科学研究通过给予感官刺激来探索大脑的活动规律,都体现了感官七窍与神的联系。而无论是从七窍与脑的位置相近,或者解剖实践与生活经验的积累都能促使人们认识到脑与七窍的紧密联系,从而结合其他实践经验以及内省认识到脑主神。如《素问·解精微论》云“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认为耳目之泣涕从脑渗出;《素问·脉要精微论》亦云“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东汉《春秋元命苞》记载“头者,神所居”;《颅囟经·序》言“元神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泥丸即脑;《说文解字》言“思,容也。从心囟声”,囟指头顶脑盖会合之处。清代王清任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也是以其观察到耳、目、鼻皆通于脑,以及小儿的脑发育与感官、记忆、语言等功能发展的同步性为基础[22]。这些都说明从感官七窍的具身经验出发,古人不仅能认识到精神、思维与心有关,亦能认识到其与脑的关联。
古代医家对于脏腑属性的不同划分决定了藏象理论的构建,在以五脏为核心的藏象理论中,心为藏神之脏;《素问·五脏别论》云“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或许在以脑为脏的藏象理论中,对主神的脏腑会形成不同看法;与《黄帝内经》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医学也存在心主神与脑主神的争论[23]。中国古代学者的重“中”思想或许是促进“心主神”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躯干与头、四肢之间构成“中心-边缘”或“上-中-下”的位置结构关系,躯干与其内的脏腑始终处于人体的中间部位。《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古代学者受到重“中”思想的影响,或出于更深层的身体观念,认为躯干及内脏与头、肢体的重要程度不同,选择从身体内部寻求神的所在而将主神的功能赋予心。感官与认知的密切联系启发了“心主神”与“脑主神”两种理论的形成,也将成为两者联络沟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两种命题可以进行简单的主语替换。因为在中医理论构建过程中,“心主神”命题在天人视域下得以不断具象化落实并从多层次延展,由抽象观念落实为具象化、实质化的医学理论[24];并且融入理法方药俱全的辨治体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6 小结对于难以通过肉身感知的脏腑功能关系,基于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同步性、相似性创造恰当的隐喻,是古代人们认识和形成脏腑相关概念及命题的基石。本文从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概念隐喻理论,辨析“心主神”理论的形成原因及其背后串联的经验事实和认知规律。阐明感官七窍与神的关系及其与心之七窍相应启发了中医“心主神”理论的构建,并从感官的认知取向发展解释心开窍之官的确立,指出感官七窍与神的联系是“心主神”与“脑主神”理论建立的共同基础。从概念隐喻理论分析“心-神-窍”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利于理解“心主神”理论的深刻内涵及价值,也是正确处理中医心脑关系的基本前提。揭示了隐喻对于中医心藏象理论构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2024, Vol. 41
2024, Vol. 41




